試想一下,如果把時序定在下一個千禧年(西元3000年),當那時候的人們聽到「六堆」這個名詞,他們會有什麼反應?他們知道「六堆」其實是台灣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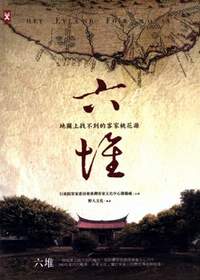 《地圖上找不到的客家桃花源:六堆》是由三位在六堆地區出生長大的客家作者,經過長期田野調查,在文字和圖像中勾勒出這塊抽象地域的存在位置。
《地圖上找不到的客家桃花源:六堆》是由三位在六堆地區出生長大的客家作者,經過長期田野調查,在文字和圖像中勾勒出這塊抽象地域的存在位置。
「六堆」不是實際的地理名詞;它原來只是屏東平原高屏溪畔的南台灣客家族群的代名詞而已。
約在18世紀初,客家先民落腳在今天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附近的地區,並以此為基地分北、中、南三路前進墾荒。向北的沿麟洛溪兩岸開墾,或溯武洛溪而上,拓展到美濃、杉林一帶。向中的主要從麟洛河下游到潮州附近,然後上溯五魁寮溪,開墾竹田、萬巒、內埔等地。向南的則沿東港溪到溪州流域,在今天的南州鄉溪南村一帶與閩南人混居。
西元1721年,朱一貴誓師抗清,卻與率眾應和的廣東籍杜君英發生權力爭奪,開始內訌。朱一貴與部下轉而攻擊屏東客家庄,燒殺搶掠。當時高屏溪兩岸的客家聚落為了保家自衛,以今天的竹田西勢村為中心,面向高屏溪方向,分成前、後、左、右、中、先鋒等六個營隊,成立客家義勇軍,統稱「六營」,後來為了有別於軍隊,用諧音改稱「六堆」,避人耳目。
歷經三百多年時空轉變,當初因禍福與共所組織的義勇軍已經解散了,「六堆」這名詞卻繼續沿用到今天。因為同語言同風俗,社群內聚力強大,屏東平原地勢完整且獨立,豐饒的糧作收成,助長六堆地區經濟與產業發展獨立卻相對封閉的特質(有此一說,當時的客家人不願與鄰近的閩南人有貿易往來,是因為雙方長期有資源爭奪戰,再加上閩南人城府深,兩個族群經常僵持不下)。
六堆的故事 躍然紙上
當然,今日的六堆早已一改保守封閉的傳統態度,尤其是在對外交通建設完成後,向外發展便利,也因為道地的客家美食,其中的萬巒、美濃等地開始成為旅遊景點。然而有趣的是,居住在此根源意識強烈的六堆長輩,仍堅持在自己的土地上必須說客家話,也正因為如此,客家文化的傳續在六堆地區,始終非常具體。
六堆的故事,令人聯想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不同的是,六堆是具體地存在於現實世界。翻開《六堆》這本書,不只交代歷史沿革,作者群更運用大量的六堆地區的宅邸、祠堂、廟宇、牌樓等建築物照片,搭配詳盡的工藝內涵的分析解說,證明了六堆的文化痕跡;因為建築物是最容易辨認的符號、也是地域性文化活動的最有力的證明。透過平穩的筆觸,六堆地區民風純樸、與世無爭的氛圍,躍然紙上、歷歷在目。
這是真的,作者群之一的黃瑞芳說,現在進入六堆,仍然可見樂天知命的男女老少,說著音韻典雅悠揚的四縣客家話,熱情地迎接外來遊客,端出道地客家菜餚,細述六堆今昔,儼然現代版的「客家桃花源」,真讓人有「來此絕境,不復出焉」的陶醉。
《食飽吂》在菜餚裡找到生命連結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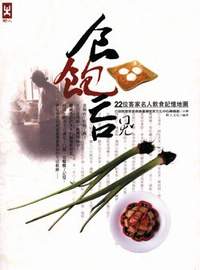 說到最基礎、最不易變遷的另一個客家文化象徵,就是客家家常菜;要了解最動人的客家庶民文化,不能不從飲食入手。
說到最基礎、最不易變遷的另一個客家文化象徵,就是客家家常菜;要了解最動人的客家庶民文化,不能不從飲食入手。
擺脫嚴肅的歷史研究,《食飽吂》是一本21位客家名人與1位和客家庄淵源極深的名人他們的「食物戀」故事集,透過訪談,以說故事的方式,娓娓道出回憶中最不能忘懷的一道客家菜;以及這些菜餚與生命的連結點。
《食飽吂》中的每一道料理都有詳盡的步驟解說與圖片示意。做為示範者,本身也是客家飲食文化推廣者的阿緞姊(鄭綵緞),近幾年才投入飲食文化的開發與研究。她認為,在商品化的衝擊下,「道地的」客家美食已經很少見到了,現在坊間標榜「客家美食」、大量生產製造的料理,已多半捨棄傳統元素,改用替代性食材,因此客家特色大減。她說,所謂的「道地」,不只食材,連製作全程也應該要遵循古法,才夠格稱作「客家料理」。所以接下《食飽吂》的工作,讓她感到對得起自己的信念、還有客家身分。
過去由於政策上的偏頗,客家文化一度有消失的危機。今日,客家文化的復興運動,已開播的客家電視台、籌備中的客家文化中心、蔚為風行的客家料理,還有每年盛大舉行的桐花祭與義民祭典,這一切,是我們的社會終於確立了多元價值觀;加上客家族群的自覺與努力,所以水到渠成。
同樣的,母語式微、傳統文化的失傳,在閩南與原住民等族群,仍是共同面臨的問題。如果你有警覺,請立刻捕捉你生存的世界;就從你腳下站的地方,開始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