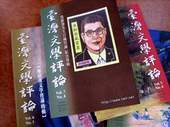隨便說個台灣名人墨士,這裡一定找得到任何隻字片語的手稿!此話一出,豪氣萬千,再望向館長張良澤桌上用來勉力對準的放大鏡,強烈感受到「台灣文學資料館」的研究價值,既非天生財力雄厚、也非人力充裕,完全是他一步一步走過台灣文學坎坷路的回報。
以建構台灣文學為矢志
 1997年,第一個「台灣文學系」在真理大學淡水校區出現,而第一所「台灣文學資料館」也同時成立。隨著藏書增加、場地日益狹窄,也為感念台灣文化起源於台南縣,「台灣文學資料館」於2002年正式遷往台南縣麻豆校區,並於同年開幕啟用。
1997年,第一個「台灣文學系」在真理大學淡水校區出現,而第一所「台灣文學資料館」也同時成立。隨著藏書增加、場地日益狹窄,也為感念台灣文化起源於台南縣,「台灣文學資料館」於2002年正式遷往台南縣麻豆校區,並於同年開幕啟用。
當時在日本任教、受邀回台負責籌辦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與創辦「台灣文學資料館」的張良澤,因無法立即辭去在日本的教職,而採取隔月返校集中授課,同時他也一邊整理分散在中、日兩地的台灣文學資料。2005年,長期埋首台灣文學資料整理工作的張良澤辭去在日本的教職,正式擔任台灣文學資料館的館長。
其實張良澤早在20歲時,就有成立台灣文學資料館的構想,「只不過,當初完全想靠自己的力量」。因為身為戰後第二代作家的他,目睹上一代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作家,雖也具有流暢的中文寫作能力,卻因處於受壓迫的陰影而難以舒展。
為再現戰後台灣作家的心路歷程,以及紀錄當時台灣社會的變化,當張良澤有機會與戰後第一代作家鍾肇政等人聚會,便抓緊時機「央請鍾老將接到的書信留著,好作為建構台灣文學資料館的史料。」他說出這段話時,只是一位景仰鍾肇政且常在《聯合副刊》發表文章的年輕作家。
幸好,「鍾老是一位很願意提攜後進的作家,也將這請求聽進心裡了。」雖然張良澤於1978年中美建交前夕,因提倡台灣文學被列為思想犯黑名單,不得不遠赴日本,但當他於1992年返台後,鍾老還是將這33年間所有與文友往來的書信交付給他。而今陳列於館內、有「台灣文學萬里長城」之稱的鍾肇政書信集,除展現作家們當時的心境,也承載著戰後台灣作家為文學打拚的痕跡,亟富研究價值。
衣帶漸寬終不悔
 館內這座「台灣文學萬里長城」,是張良澤所樂於津津樂道的,不只是研究台灣文學的珍貴史料,更為戰後第一代作家信守承諾的美談。台灣文學資料館的展示空間共規劃三大部分,為:「作家手稿」陳列作家手稿、原住民圖片、和名人題字等第一手資料;「日治時期文獻」擺設當時台灣文學雜誌及重要作家的專櫥;以及「戰後時期與鄉土教育」則有戰後至今重要的文藝刊物。
館內這座「台灣文學萬里長城」,是張良澤所樂於津津樂道的,不只是研究台灣文學的珍貴史料,更為戰後第一代作家信守承諾的美談。台灣文學資料館的展示空間共規劃三大部分,為:「作家手稿」陳列作家手稿、原住民圖片、和名人題字等第一手資料;「日治時期文獻」擺設當時台灣文學雜誌及重要作家的專櫥;以及「戰後時期與鄉土教育」則有戰後至今重要的文藝刊物。
至於書庫的藏書方面有,「西川滿先生紀念文庫」收藏於第一書庫;「郭榮桔先生紀念文庫」佔滿了第二書庫;旅日學者吳進義教授、張良澤教授及其他日本友人的贈書皆收集於第三書庫。無論是展示空間裡的文獻資料,亦或是受贈的書庫藏書,約略可判斷這些台灣文學史料得來之不易。
從時間的縱軸來看,台灣文學長期因政治、地緣因素,常被視為邊陲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在發展上受到相當大的壓抑;再從資料的廣度分析,散落到日本的台灣史料、原住民照片,皆因張良澤投入極大心力收集,而有資料面向愈益寬廣的態勢。
「在日本舊書店,只要看見與台灣相關的都買。」張良澤表示,自己薪水「只有」一半以上花在購買與台灣相關的資料,卻又不經意提到「有時錢帶不夠,書店老闆還會因為是熟客,而讓我賒帳哩!」由此可見,他不僅專事台灣文學研究,還以發揚台灣文化為終身職志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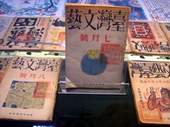

史料漸豐置四方
然而,眾多台灣文學史料的進場機制,因張良澤的苦心收集而顯得無懈可擊,不過,收集之後的整理、分類、再陳列的過程更是一大挑戰。「赴日前,租來的小屋無法安置這一大堆的台灣文學史料,而暫放好幾位親戚家;赴日回台後,運回的好幾貨櫃的資料因台灣文學資料館的設立,而有了安身立命的處所。」當尋訪展示空間時,眼睛所見的不只是資料原本的研究價值,還隱含它流離失所、差點淹沒在荒煙蔓草中的經歷。
而今「台灣文學資料館」雖座落在真理大學麻豆校區內,卻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還是以台灣文學史料的蒐集、促進台灣人文的意識來自我定位。校方除規劃空間做為展示、提供研究,對於藏書的增設則沒有編列任何預算,「反正原本就打算靠自己的力量成立,沒購書預算就自己買,待資料整理、研究完後,再捐出歸公。」這是張良澤埋身在台灣文史資料中,不知疲累、不計付出的堅持。
而今年已邁入第十一年的「牛津文學獎」,除表揚對台灣文學有貢獻的作家,作家們以此為榮而捐贈個人著作,以豐富館方設立專櫃的佳事,也時常有所聞。隨著得獎者歷年增加,館內的藏書也日益豐富,值得一提的,還有館內另有歷屆得獎者的揮毫作品。第二屆牛津文學獎得獎者葉石濤以樸拙字跡寫出「我的信念」:我一向相信文學是身上之鹽,鹽,原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但,對我們身體健康原是必須的……。在細覽作品之外,在館內透過字跡感受台灣文學家的精神,更為深刻。
張良澤提及掛在戰後台灣文學史料區一幅由戰後第一代作家鍾肇政親筆寫的《戰後文學的發展史》,「鍾老從未寫過那麼多書法字,在寫得時候氣喘又犯,喘的時候就休息、休息完再寫,可說是用生命寫出來的。」要不是他與鍾老幾十年的交情,這幅又長、又別具意義的墨寶,可能就不會出現了。
當我們隔著一層紗,來看台灣的文學美景始終有一種置身事外的美感;但當我們貼近台灣文學的整理與考究,再探究其在時代夾擊中面臨著嚴峻挑戰,仍試圖以更創新的面貌繼續蓬勃再生的真相,令人動容。
看見展示間內還有一箱尚待整理的資料,讓人想起張良澤拿起放大鏡、勉力對準的模樣。當他從一位創作者、學術研究者到教授,最後以一位文學史料的蒐集、編輯者來自我定位,台灣文學也因為有他扎實、細密的學術功夫,而奠定堅若磐石的研究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