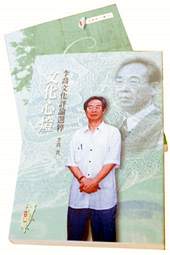在大愛與大恨中翻騰
走出番仔林 跨越人性的隘口
寒夜漫長從不曾迷惑
文學是恆定的北極星
數百萬文字如雨降落
在臺灣的土地匯成巨流
哲理思辨曲折彎繞
死亡苦難穿越而過
您的智慧是海
廣闊,且是最終的贖救
──真理大學謹獻給李喬先生
 由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舉辦的「台灣文學家牛津獎」迄今已邁入14屆,多年來獲獎者皆為臺灣文學巨擘級人物,例如:鍾肇政、王昶雄、廖清秀、黃靈芝、鄭清文等諸位臺灣文學名家,2010年由「大地之子」客籍文學家李喬拿下獎座,可說是實至名歸。
由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舉辦的「台灣文學家牛津獎」迄今已邁入14屆,多年來獲獎者皆為臺灣文學巨擘級人物,例如:鍾肇政、王昶雄、廖清秀、黃靈芝、鄭清文等諸位臺灣文學名家,2010年由「大地之子」客籍文學家李喬拿下獎座,可說是實至名歸。
為了讓更多人瞭解臺灣文學價值史觀,頒獎之後,主辦單位精心安排李喬文學學術研討會,從不同層面,剖析李喬的文學價值地位,透過互動對話,擴大臺灣文學研究視野。
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館長張良澤以「臺灣獨立建國後,第一位拿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家,必是李喬。」一言道破李喬對臺灣文化獨立運動貢獻的殊榮。
李喬,本名李能棋,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鄉境的蕃仔林。父親是「隘勇」出身的抗日農民運動家,在日治時期,不是被捕就是逃亡,持家重擔全落在母親身上,加上從小生長環境貧困,影響李喬日後的寫作風格與價值觀,而對臺灣這塊土地的意識覺醒也是從這裡開始發酵。李喬說:「我是樸素的左派分子,我的臺灣意識來自普羅階級的貧困生活,自小就是山中的窮農,唯一能掌握的就是這塊土地,我和土地間的情感是如此緊密,愛土地的想法自然也就跟著形成,不是刻意鋪成的結果。」
不平凡的反叛者
有人說李喬是座深不可測的山,那麼想探索李喬這座高山,就必須從他的短篇小說開始切入。李喬花了約20年的創作生涯去經營200多篇的短篇小說,也是他用來建構自己文學世界的礎石。
回溯這些短篇小說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李喬用千變萬化的寫作形式、技巧及題材去經營他的作品,令人難以捉摸。文學家鄭清文用「鋼索的高度」形容李喬,他是一個走鋼索的人,走過被炸毀的美國雙子星大廈,也走過尼加拉瓜瀑布,在陣陣風中,還會抬起一隻腳,快樂地在鋼索上搖擺,這就是李喬。他喜歡不斷嘗試、不斷挑戰,不安於平凡,意圖寫出別人不曾寫過的文章,在作品〈修羅祭〉中李喬就創了5個不平凡。「第一個不平凡,一般的狗看到人會搖尾,現在臺灣有很多會搖尾的狗,但李喬的狗卻露出兇牙利齒,隨時會咬人;而這隻兇狠的狗後來被打死了,也很不平凡,因為要保護動物不能打狗;不僅如此,還拿去做香肉賣;煮了送一碗給李喬吃,你們猜李喬吃了沒?吃了。誰會這樣寫!基本上李喬是一個不平凡的反抗者,他在〈修羅祭〉裡吃了那隻兇猛的狗,他要把牠變成自己的血肉,繼承牠反抗的精神。」
在另一篇1973年的作品〈孟婆湯〉中,一名煙花女子劉惜青,在床上交媾之際,被人勒頸斃命。一縷冤魂到了冥府第十殿,鬼王宣判,被害人障業紛紛,身為妓女,罪加一等。像這樣不明事理的鬼王,只判被害人不判加害人,若與現實對照鬼王的行為不就是對顢頇無理政府最好的寫照。鄭清文用半調侃的方式說,這就是李喬狡猾的地方,他有很多短篇小說是出自戒嚴時期的作品,用隱喻的方式,才不會被抓。「其實李喬是很孤獨的,在那個年代寫批評政府的文章,可能會被捕入獄。用高超的暗喻手法寫作,或許喜歡看包公案的人會懂李喬的作品,不過把蔣介石稱呼為蔣公的人一定無法理解李喬的作品,就連情治人員也看不懂,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
臺灣人的土地苦戀史
 走過了壓抑年代,原本視為禁忌的政治話題,瞬間變成百無禁忌的家常言談。此時李喬打開筆罈,走入長篇小說的年代,通過歷史隧道與臺灣土地發生一連串緊密的連結,也就是《結義西來庵》的誕生,一個描述1915年噍吧哖武裝抗日的故事。
走過了壓抑年代,原本視為禁忌的政治話題,瞬間變成百無禁忌的家常言談。此時李喬打開筆罈,走入長篇小說的年代,通過歷史隧道與臺灣土地發生一連串緊密的連結,也就是《結義西來庵》的誕生,一個描述1915年噍吧哖武裝抗日的故事。
李喬曾在自剖自己的文學生命時說過:「我選擇寫作余清芳,結果對我一生發生決定性的影響。」他閱讀300多萬字的《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資料,學會了梳理史料、重建歷史空間的本領,更重要的是確立自己是個臺灣小說人的身分。「我是誰?我是什麼人?哪裡的人?我不是誰?我不能是誰?凡此這些,瞬間以一道靈光貫穿我內外。我透明了,我那屬於臺灣人的『任督二脈』霍然貫通。」
而1977年至1981年完成的《寒夜三部曲》,是一部描寫細膩的大河小說,也是李喬生平的代表作。由3部小說集結而成,《寒夜》寫的是土地,《荒村》說的是臺灣人民抵抗不義強權的事跡,《孤燈》則是描述回歸故鄉與大地合一的故事。
李喬用108萬個字刻劃半個多世紀臺灣庶民百姓的土地苦戀史,寫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抗爭,也不問民族國家大義,是來自生活的反抗,為土地、為生存承受苦難,奮勇爭鬥的歷史,一個人類生命內在的情懷。李喬在《我的心靈簡史》書中表示,「領會、領悟人與土地的愛恨喜悲、土地與生命的連結、生命土地的究竟──由寫作而萌生、形成、成型的過程,貫串了我文學生涯的全程,也是一生思行的總結論。也據於此,形成我的臺灣人意識、臺灣意識;也真正是追求臺灣自主前途的基底所在。」
另一部《環之咒》長篇小說,則是李喬臨老之作,也是歷史系列最後一部小說。小說題名源自知名學者李鴻禧當年說的「臺灣人,是受詛咒的民族!」真理大學蔡造珉教授說:「這是多麼嚴肅沉痛的指控啊!沒有人願意去詛咒自己的國家,就如同沒有人會去詛咒自己的母親般,這五味雜陳的複雜心情如同李喬對這片土地沉痛的認知。」李喬也才會在書中聲明,天下無白吃的午餐。臺灣人追求自己的自由,輕鬆的舉手或投票,不須流汗流血?不可能的。但並非絕望,李喬最後帶著有情的張望,留下對臺灣的警惕與反省。
朝文化臺獨路前進
談到李喬的作品,除了小說外,當然也不能錯過鞭辟入裡的文學論述,李喬離開堅守近30年的小說家位置,是從《臺灣人的醜陋面》開始,這是一本解剖臺灣社會文化的文學論述。李喬在解構批判同時,也反思、建構臺灣文化走向。後來的《臺灣文化造型》、《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和轉機》到最新出爐的書籍《我的心靈簡史──文化臺獨筆記》,在在顯示出李喬想保衛臺灣這塊母土的決心。
望春風出版社發行人林衡哲表示,李喬在臺灣戰後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愛爾蘭的葉慈與美國的愛默生。「我深信有一天李喬的《我的心靈簡史──文化臺獨筆記》也是臺灣文化的獨立宣言。他在書中的結論,臺灣文化獨立是唯一幸福前景。將是21世紀臺灣人共同的夢想。」
過去,李喬筆耕不輟,用數百萬字完成無數撼動人心的臺灣文學作品。未來,這位出身山城小村的作家,要用「世界體系、在地主義」喚醒讀者對這片土地的尊重。李喬說,薩依德曾在《文化與抵抗》中提及朋友所講的一句話,巴基斯坦人所面對的敵人是一個曾在歷史上受盡災難、被人欺負的國家,也就是以色列。反觀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也是如此,中國其實是一個長期受壓迫、傷害的國家,它現在壯碩了,就開始對外發展欺負臺灣、新疆、吉貝特等國家,令人心痛!將來人類追求的體系不再是政治、經濟…,是一個生態體系的保衛概念,尊重多元、平等且開放的在地發展。
閱讀李喬,不單單只是閱讀臺灣人尋求主體及反抗殖民的歷史,也是建構臺灣文學與文化在地化的起點,值得慢慢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