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來自現實的生活,也來自詩人個人生命情調的再現。從事新詩創作40餘年的林仙龍,最近把他於1989年出版的詩集《眾山沉默》再加以修訂整編,並分為9卷,共收158首詩作,以《每一棵樹都長高》為書名,交由高雄春暉出版社出版;然而,面對《眾山沉默》出版時已收有140多首作品,至今僅新增十多首作品,可見近20年來,林仙龍的詩創作是歉收的。
對於林仙龍決定把第一本詩集也是唯一的詩集整編出版,他認為一方面要對昔日再作一次深情面對,另一方面,也針對當年詩集收錄略嫌蕪雜,以及文字未盡之處,再作一次完整的呈現。從《每一棵樹都長高》詩集,讓我們驚見林仙龍寫作技巧的完整性與主題的一貫性。詩中所彰顯的心靈世界是山與海的對話,是成長過程知性與感性的交融,更是個人生命情調的抉擇。
 林仙龍出身鹽分地帶,那兒有鹽田、漁港的體味,那兒有稻田、蔗園的芳香,雖然鹽田、稻田、蔗園大多已廢耕,但是這都是童年記憶,詩人就從童年往事入詩,至今依舊在詩中對話。1967年林仙龍保送政工幹校,參加「復興崗寫作社」,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包括新詩、散文、小說。政工幹校畢業後分發到海軍陸戰隊,從此與海脫不了干係,因此童年的海與職場上的海相結合,所以詩集的卷二〈走進大海的風暴〉,敘說著有關海的種種,是童年記憶的描繪,刻劃漁村討海人的生活:孩子們出海後;母親依然在院子裏/補漁網。黃昏的時候/送爸爸的竹筏出海/深深的夜裏/讓浪濤擊潰/啊啊,我們都在孤獨的/討生活;我們都在傷口上/為著不忍吐露一聲/感嘆;在職場的海上記事,述說著航行中領略生命的真諦:看海上漁火點點/看時光在濤聲中退走/一遍又一遍,你習於為大海/沉默。你習於為大海守望/偶然,濤聲回來應答/偶然,濤聲一路號啕/大風大雨來了。對於童年與職場上海洋的情境交融,我們可就〈夢的漂浮〉這首詩來體會作者的生命情調:我的夢不在沙灘不在岸邊。我的夢是茫茫歲月/來不及認識,來不及捕捉;一灘腐壞的。蛋黃/濃稠、潮濕並且紊亂。另外,在〈海邊的石頭〉也作如此的告白:行船的人回來了/行船的人回來看海邊一塊眺望的/石頭。彷彿剛從風中雨中走來的/一塊石頭;還有昔日一滴一滴/遺落的,淚。這兩首詩皆反映了童年往事到職業軍人的海上生活,歷經不如意的過往,在人生歷程留下深深的刻痕。
林仙龍出身鹽分地帶,那兒有鹽田、漁港的體味,那兒有稻田、蔗園的芳香,雖然鹽田、稻田、蔗園大多已廢耕,但是這都是童年記憶,詩人就從童年往事入詩,至今依舊在詩中對話。1967年林仙龍保送政工幹校,參加「復興崗寫作社」,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包括新詩、散文、小說。政工幹校畢業後分發到海軍陸戰隊,從此與海脫不了干係,因此童年的海與職場上的海相結合,所以詩集的卷二〈走進大海的風暴〉,敘說著有關海的種種,是童年記憶的描繪,刻劃漁村討海人的生活:孩子們出海後;母親依然在院子裏/補漁網。黃昏的時候/送爸爸的竹筏出海/深深的夜裏/讓浪濤擊潰/啊啊,我們都在孤獨的/討生活;我們都在傷口上/為著不忍吐露一聲/感嘆;在職場的海上記事,述說著航行中領略生命的真諦:看海上漁火點點/看時光在濤聲中退走/一遍又一遍,你習於為大海/沉默。你習於為大海守望/偶然,濤聲回來應答/偶然,濤聲一路號啕/大風大雨來了。對於童年與職場上海洋的情境交融,我們可就〈夢的漂浮〉這首詩來體會作者的生命情調:我的夢不在沙灘不在岸邊。我的夢是茫茫歲月/來不及認識,來不及捕捉;一灘腐壞的。蛋黃/濃稠、潮濕並且紊亂。另外,在〈海邊的石頭〉也作如此的告白:行船的人回來了/行船的人回來看海邊一塊眺望的/石頭。彷彿剛從風中雨中走來的/一塊石頭;還有昔日一滴一滴/遺落的,淚。這兩首詩皆反映了童年往事到職業軍人的海上生活,歷經不如意的過往,在人生歷程留下深深的刻痕。
從林仙龍詩作的內涵可發現是知性與感性的結合,這種感知的形成,是一種「自我教養」。英國藝術家佩特(Walter Pater)說:感受性的培養是唯一能賦予生命意義又能完全涵蓋生命的事物。在〈每一棵樹都長高〉這首詩,如同第一卷「如果我也要成為一座高山」中的作品一樣,是感知的展現,是言志的期許,是自我的鞭策。詩作描繪:
漫山遍野的葉子
隨著一陣風
變換隊形;隨著一陣風
滿山遍野踩過的步子都成了紛飛的葉子
滿山遍野粗大的葉子都循著步聲回來
尋找一棵樹
詩中展現自我期許:循著步聲回來尋找一棵樹,這棵樹會長高。同樣地,在〈空原的小樹〉說:一顆種子不願意多說一句話/許多人都在夢中守住一句話。種子不說話跟夢中守住一句話,作者具現了人生的無奈。林仙龍往往以生活的片段來書寫生命的缺口,於〈水手〉一詩,如此描繪海上生活:後甲板上,風起了/整個大海歪歪斜斜。滿滿的皺紋/像艙間吊床得一席床單/他點燃了一支煙/吸兩口;他把煙熄滅/時間短促/像一個人的嘆息//大海,來/我們都要忘記/且看一艘船駛過茫茫的大海/且看一艘船看著遠方天際的/一顆星。詩中充滿水手海上生活的孤單和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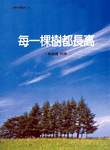 雖然《每一棵樹都長高》這本詩集,其主旋律是個人生命情調的再現,但在卷七「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一些臉」的詩作,出現了現實社會的描繪,描繪了軍人、攤販、油漆工、磨刀匠、老工友、伐木工人、農人等下層社會的群像,卻充滿詩人個人的抒情調調,無法聚焦職業別的人物分野,而真正展現敘事性特色的,卻在卷九〈阿土伯的黃昏〉一詩,成功地表現現實農村的敘事性。另外,林仙龍以小說的手法展現在詩作的,〈離異〉一詩可說是傑作:
雖然《每一棵樹都長高》這本詩集,其主旋律是個人生命情調的再現,但在卷七「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一些臉」的詩作,出現了現實社會的描繪,描繪了軍人、攤販、油漆工、磨刀匠、老工友、伐木工人、農人等下層社會的群像,卻充滿詩人個人的抒情調調,無法聚焦職業別的人物分野,而真正展現敘事性特色的,卻在卷九〈阿土伯的黃昏〉一詩,成功地表現現實農村的敘事性。另外,林仙龍以小說的手法展現在詩作的,〈離異〉一詩可說是傑作:
讓他去吧
讓他……衰弱如一片落葉;若干年前
他走了。在窗口停頓的
泣聲,夾雜一些
恨……。喧騰如一陣風
逝去
幾年了,她在小城的另一個樓台
晾尿片;見到他
獨步的身影,風一般的
詭譎。風一般的
仍有怨
這不便稱呼的
男人;如果仍是一片葉子
天際冷闊,隔著
兩片翻飛的姿勢
沉沒
從這首敘事詩,詩中的情境雖是虛擬,但是充滿人生命運的缺口,依然流盪著抒情的調調,這就是林仙龍的個人生命情調的具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