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南台科技大學教授林柏維日前應邀至台灣文學館發表演講,該講座係為配合「民國一百年,閱讀蔣渭水」特展而舉辦。
 此次演講內容雖以「蔣渭水與臺灣新文學」為題,但林教授認為:嚴格來說,蔣渭水是政治家,他的作品也多偏向政論性質,呼籲政治社會改革思想,與文學有關聯的作品幾乎皆在牢獄書寫。蔣渭水作品極富政治色彩,被殖民、被壓迫的反抗精神貫穿其中,成就其牢獄文學風格,樹立起蔣渭水式的抗議文學。蔣渭水,興文化啟蒙風雲,做政黨政治先鋒,建農工運動之生機,為臺灣文學推波助瀾,其文學風采不在典範,而在先行。(本文為林教授演講內容摘要)。
此次演講內容雖以「蔣渭水與臺灣新文學」為題,但林教授認為:嚴格來說,蔣渭水是政治家,他的作品也多偏向政論性質,呼籲政治社會改革思想,與文學有關聯的作品幾乎皆在牢獄書寫。蔣渭水作品極富政治色彩,被殖民、被壓迫的反抗精神貫穿其中,成就其牢獄文學風格,樹立起蔣渭水式的抗議文學。蔣渭水,興文化啟蒙風雲,做政黨政治先鋒,建農工運動之生機,為臺灣文學推波助瀾,其文學風采不在典範,而在先行。(本文為林教授演講內容摘要)。
蔣渭水,1891年於宜蘭出生,醫學校畢業。1921年,以一篇〈臨床講議〉為臺灣開出第一張診斷書立下醫學文學典範,後雖因治警事件入獄,依舊不畏政治壓迫繼續執筆針貶時政,寫下〈快入來辭〉、〈入獄日記〉、〈獄中隨筆〉、〈北署遊記〉等多篇牢獄文章,樹立起蔣渭水式的抗議文學風格,開啟了臺灣人權文學、監獄報導文學的新頁。1920年代,蔣渭水和他所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為臺灣掀起各式社會運動波濤,催化民族意識的普遍覺醒,同時為臺灣新文學推波助瀾。綜觀蔣渭水其文學風采,不在典範而在先行。
文化、民主運動先行者
1920年代,受到全世界鼓吹提倡民族獨立、民主自決等思潮影響,臺灣在東京的留學生為鼓吹獨立自主,先後成立啟發會、新民會等組織,並創刊《臺灣青年》,1922年更名為《臺灣》,同時發刊《臺灣民報》。深受感召的蔣渭水認為,臺灣知識份子不該以此為滿,應更積極推動,他個人不僅出任《臺灣》董事,並創立文化公司,引進文化、思想方面之圖書報刊;以政治、新聞報導為主的《臺灣民報》在遷回臺灣印刷發行後開闢文章寫作版面,為日後新文學創作預留園地。
1921年10月,蔣渭水在他所開設的大安醫院成立台灣文化協會,除了出任專務理事,同時找來林獻堂擔任總理,協會成員主要來自地方士紳、海外留學生以及本土知識菁英。在蔣渭水的主導下,文化協會全力推動文化啟蒙,掀起20年代各式社會運動浪潮。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發展迅速,分別於臺北、臺南、彰化、員林及新竹成立支部,並全力支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這也引來臺灣總督府採取壓制措施。1923年「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當局便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對會員展開大規模拘補,包括蔣渭水在內等13名重要幹部被判刑,此即為著名的治警事件。遭拘捕者雖被視為英雄,然而受治警事件影響,林獻堂等許多文化協會會員陸續被迫退出,1,000多名會員最終只剩600多人。身陷牢獄的蔣渭水則繼續執筆為文批評時政。
開啟臺灣醫學文學
 曾任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發行人的蔣渭水,於1921年11月《會報》首期發表名作〈臨床講義〉。文中他發揮醫學專長為臺灣這名患者徹底把脈開出第一張診斷書,就其姓名、性別、年齡、原籍、職業、遺傳、素質、既往症等基本資料填寫敘述之餘,更直指病因。蔣渭水診斷臺灣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原因則來自於「智識的營養不良」,而「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正是他為臺灣所開出的五味藥方。〈臨床講義〉充分展現蔣渭水醫國也醫民的決心與精神,不僅被喻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經典之作,更被視為臺灣醫學文學的開端。
曾任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發行人的蔣渭水,於1921年11月《會報》首期發表名作〈臨床講義〉。文中他發揮醫學專長為臺灣這名患者徹底把脈開出第一張診斷書,就其姓名、性別、年齡、原籍、職業、遺傳、素質、既往症等基本資料填寫敘述之餘,更直指病因。蔣渭水診斷臺灣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原因則來自於「智識的營養不良」,而「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正是他為臺灣所開出的五味藥方。〈臨床講義〉充分展現蔣渭水醫國也醫民的決心與精神,不僅被喻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經典之作,更被視為臺灣醫學文學的開端。
新舊文學交手
1922年,陳端明發表一篇〈日用文鼓吹論〉,正式將臺灣語文使用問題浮上檯面;同年,謝春木在《臺灣青年》發表日文小說〈她往何處去〉,開啟了新文學的創作,而“她",指的正是新臺灣。1923年,治警事件的發生促使張我軍認為要建設臺灣新文學,非得打倒舊文學不可。他首先以〈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祭出批判,接著以〈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正式向舊文學展開攻擊,震撼當時臺灣文壇,為臺灣文學史上首度新舊文學論戰揭開序幕。
新舊文學筆鋒交錯攻擊的同時,也啟發了新文學創作,例如:施文杞的〈臺娘悲史〉、賴和的〈鬥鬧熱〉、楊雲萍的〈光臨〉、張我軍的〈買彩票〉等小說,而張我軍的《亂都之戀》更是臺灣第一本現代詩集。新文學創作的出現,使得臺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日漸具體化。


蔣渭水式的抗議文學
因治警事件數度身陷牢獄的蔣渭水,期間陸續於《臺灣民報》發表多篇作品並獲得不少迴響。其牢獄文章約可分為仿古之作、日記隨筆兩類,他的文章風格,也正好反應出臺灣新舊文學之演變。
(一)仿古書懷:在擔心文字獄的心理壓力下,早期身陷牢獄的蔣渭水藉古文型式抒發心情,把不能說的話寄寓原作旨意,行藉題發揮、藉古諷今之實。文章雖為仿古之作,卻仍不失為創作。例如:仿陶淵明〈歸去來辭〉的〈快入來辭〉,文中寫道「快入來兮,心園將蕪胡不入,己自以身為奴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入,知來者猶如仙,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入即是,不入即非)。」略有幾字與陶原作有差異應是記憶力所致。
接著,對照陶淵明在原文形容田園生活之恬適自得,蔣渭水則敘述牢獄生活之苦中作樂,而一句「我有志而難成」,不僅一語道盡內心苦悶,結尾更以「策士同以歸正(世界大同同歸正義),共扶人道復奚疑。」傳達心中理想。
〈送君入監獄序〉則仿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借文章脈絡為王敏川之入獄壯行,讚美其慷慨入獄不同流合污的高貴情操。仿〈赤壁賦〉的〈入獄賦〉,相較於蘇軾在原文裡對洞簫聲之精彩形容,蔣渭水則以蚊聲比喻嘲諷總督田健治郎,並以此勸戒繼任的內田嘉吉總督,蚊聲與洞簫聲的反向比喻,極具衝突性,令人拍案叫絕。
仿劉禹錫〈陋室銘〉的〈牢舍銘〉,先是將牢舍比陋室,自我調侃一番,最後以「宋朝三字獄,代周公冶刑,多人云:『何罪之有?』」,直指批判當局以違反治安警察法之藉口,行文字獄之虐政。
而在〈春日集監獄署序〉(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一文中,蔣渭水更是直接表達對臺灣前途之感慨:「會臺北之監獄,論臺灣之政事。感慨悲歌,皆為燕趙,吾人動作,獨慚印鮮」,意指同為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相較於印度、朝鮮獨立運動聲勢高昂,臺灣豈可落於人後?
(二)日記隨筆:蔣渭水的日記、隨筆皆以白話文書寫,發表於《臺灣民報》,前期3篇:〈入獄日記〉、〈入獄感想〉、〈獄中隨筆〉,後期則有〈北署遊記〉、〈三遊北署〉以及〈女監房的一夜〉。前期主要敘述牢獄生活、同志間相互關懷情誼以及對家人的思念,例如〈入獄日記〉提及收到林獻堂的慰問品:「見其物如見其人,觸物的時生出一種懷慕的感想」;後期則轉向對獄政的觀察與批評。日記、隨筆這類記錄型式章或可類比為報導文學,具歷史保存意義。蔣渭水的牢獄文章為他樹立起個人抗議文學風格,學者林瑞明即曾表示,蔣渭水並非文學家,但因其牢獄作品,使之能在臺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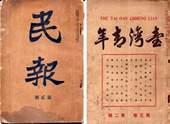


(註:「民國一百年。閱讀蔣渭水特展」於7月13日至8月29日將於國立臺中圖書館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