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口袋掏出一小罐玻璃瓶,接著輕輕地晃呀晃的,人稱老爹的黃森蘭要人猜猜看「這裡頭裝著多少菸葉的種子?」想了想又猜了猜,答案揭曉,是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的「2萬顆。」接著又將如何使相當於一瓶蓋的種子,均勻地撒在一甲地?繁複的數學公式還在跑著一甲究竟多大面積時,那還有餘力思考撒種的問題。
這時,3年7班世代的黃森蘭得意洋洋地解釋:「1瓶蓋的種子,加上2瓶蓋的沙;再將融合後的3瓶蓋,加上6瓶蓋的沙……,循著1:2的比例一直調配下去,種子就能均勻撒在土地上了。」當他剛從金融業退休,從父親口中得知這項老祖先的智慧,既佩服又不可置信的表情,與一旁幾乎呆掉的聽眾沒有兩樣。
難怪旗美社區大學要在課程手冊上印著「農村是一所學校」7個大字了。不過,身為全台第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張正揚卻在剛接下主任一職時說:「這裡的土適合作物生長,不適合社大生長。」7年過去,農村辦學侷限所導向的結果為何?實在耐人尋味。
立足農村造就社大特色
 社區大學的選課須知中明訂,正式選課者須年滿18歲,這對於人口外流嚴重的農村而言,缺少青少年區塊的人口,要招生談何容易?加上居住在當地的年長者,終其一生以務農為業,教育程度多以小學畢業為多,「雖然社大曾針對課程的銜接多做嘗試,成效仍相當有限。」綜合上述的年齡與教育程度限制,張正揚認為,能鼓勵居民坐在同一個地方上課2至3個小時,就是很大的挑戰。
社區大學的選課須知中明訂,正式選課者須年滿18歲,這對於人口外流嚴重的農村而言,缺少青少年區塊的人口,要招生談何容易?加上居住在當地的年長者,終其一生以務農為業,教育程度多以小學畢業為多,「雖然社大曾針對課程的銜接多做嘗試,成效仍相當有限。」綜合上述的年齡與教育程度限制,張正揚認為,能鼓勵居民坐在同一個地方上課2至3個小時,就是很大的挑戰。
其他還有交通與經濟的問題。幅員廣大,讓講師與學員的往返交通相當不便;需繳交學分費,更引發當地居民有花錢找罪受的疑慮。因此,旗美社大為克服交通問題,將上課地點深入到各個聚落,「只有約10%的課程開在校本部。」也是旗美社大建立學校家園的展現。
除此之外,旗美社大還將農村地區開課的諸多限制,轉換為課程的特色。成立第8年,學員多穩定維持在7百至8百人間,依「立足農村、服務農村;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的立校精神,設立農村與農業學程、環境與健康學程、社區與成長學程以及族群語文化等四大學程。
將旗美社大定位為農村型社大,是當地居民自我的認知。儘管如此,「旗美社大關注的不只是與農業相關的課程,而是與整個農村生活相關的一切。」張正揚提醒農村涉及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而非只有農業。翻開依照社區居民與學員意見規劃的課程會發現,與農業技術直接相關的課程不多,反而是與生活其他面向相關的較多。
社大體制促成有機栽種
住在高雄縣旗山區的黃森蘭,父親種香蕉的資歷,可從他小時候到退休開始算起。
笑稱「不看這吃穿」的他,直到退休後試著投入栽種才驚覺,「自己竟不識香蕉的天敵—橡皮蟲。」他如法炮製父親將晒滅得混著好年冬的手法,不夠就再加,一心只想置橡皮蟲於死地,否則一年辛苦的付出終將成空。
黃森蘭退休前一年,旗美社大剛好成立,為了從金融行業轉換到蕉農的路更順遂,他選擇到社大修習趕得上潮流的「有機蔬果班」。他永遠記得講師在認識農藥課上驚險的試驗過程,他們抓了一條蚯蚓做實驗,當牠穿過噴灑農藥的區域約10分鐘後,漸失生命跡象,最後死亡。
這一幕,激起黃森蘭對農業用藥的思考,也扭轉長久以來依循父親使用農藥的作法。「回家後,自己也抓了蚯蚓來試,嚇得連囤積的農藥都不敢再用,只好長期展示在倉庫,作為警惕。」多虧荖濃溪有機農產運銷合作社理事主席徐華盛,也就是當時做試驗的講師,讓他對農業發展有不同的體會。
與黃森蘭一樣,以旗美社大為基地,進而導入農村新思潮的人還真不少。其中,因參加有機農業學習班結識而組成的「蔓花生家族」,就是甲仙地區農民的自主性組織,理念相合又怕散掉的他們,以此來延續社大同學的情誼。當每一位農民娓娓道出,老祖先傳承智慧的體驗,以及經由多次實驗而發明出的技術,都很精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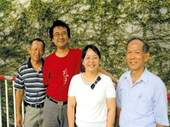


精采的新農民故事
原本在台北從事工程行業的林明賢,在2000年退休後,回到高雄縣三民鄉與家人一起在山上種植農作物。經過旗美社大有機種植課程的洗禮後,他堅持以回歸自然的方式種植,例如:梅子樹不需要太多日照,就種植檳榔來遮陽,採取「混植」提供生態相互制衡與調合的場域。在實現「不施化肥」、「不用除草劑」純淨農法的路上,他曾投入一大筆資金卻如石沉大海,但他並不孤單。
將近60歲、擁有一臉白細膚質的柯文賢,在甲仙鄉以有機方法種植近百種香草,還將過往與化工相關的專業知識加以運用。從國際化工大廠退休後,他遷居至甲仙鄉的山上就近照顧母親,歷經多次種植香草的失敗經驗,終於找出適合該地環境氣候的香草植物,並進一步開發出酵素、醋、保養品等加工產品。一次又一次的試驗與化驗過程,從未消耗掉他對開發香草產品的熱情,「有回,將自行研製的紅柚酵素送到屏科大化驗,高達87%抗自由基的含量,連自己都嚇一跳。」
還有一位讀書人出身,過去對於有機概念多來自於媒體的相關報導,直到目睹慣行農法的農友不遵守安全使用期限就將農產品賣出、鄉人因過度使用農藥而致死的諸多事例後,他決定返鄉務農。當古文錦頂著台大經濟系的學歷投入有機種植,過去所學的一切歸零。他以書上吸收的專業知識,依照書本上的相關資訊去種植,並且到旗山區社區大學進修起步。
無論是手工採收六、七分熟梅子以瓦斯爐加熱陶甕,將100公斤梅子熬煮出約2公斤純淨梅精的林明賢;或是歷經多次種植香草失敗,還是持續不懈一試再試直到成功的柯文賢;還是透過閱讀、請教、實作,逐漸掌握整個耕作流程與銷售的古文錦,他們都是高雄縣美濃、三民、甲仙地區的新一代農作者。
「社區支持農業」 逐步實現
 以高雄縣旗美社大為基地的新農民有很多,雖然各自的生產類別不盡相同,但是,透過「自願互利、共產共銷」的合作化機制,讓農民、土地與消費者一同成長的心意卻是一致的。兩年前,旗美社大發起的「農民市集」,提供農民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的平台,並鼓勵都市伙伴走入農事現場,就是此精神的雛型。
以高雄縣旗美社大為基地的新農民有很多,雖然各自的生產類別不盡相同,但是,透過「自願互利、共產共銷」的合作化機制,讓農民、土地與消費者一同成長的心意卻是一致的。兩年前,旗美社大發起的「農民市集」,提供農民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的平台,並鼓勵都市伙伴走入農事現場,就是此精神的雛型。
「農民市集只是社區支持農業的一部分。」張正揚希望能以旗美社大為輻輳點,實現「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並建立起「地產地銷」的區域型消費概念。主要強調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關係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農場餵養人們、人們支持農場,並共同分擔潛在的風險與收成。
目前美濃地區的農民已逐步計畫與高雄第一社大共同辦理「社區支持農業」的產銷模式。不過,旗美社大城鄉交流召集人、荖濃溪有機農產運銷合作社理事黃森蘭認為,「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雖然目前願意加入的農民有十多位,但生產端的品項要如何畫分與整合?穩定的產銷關係如何建立?都要納入考量。然而,「因旗美社大為非營利單位的角色,而面臨能力與資金不足的侷限。」對旗美社大來說,籌辦農民市集或是實現社區支持農業都是學習的過程,如何形成農民與消費者間緊密互動的社會網絡,還是有賴當地居民的支持。
至此,身為第一所農村型的旗美社大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也是旗美社大講師李宜欣以一句話來表示,「是一個提供不同世代對話的場域。」因為如此,居民對於扮演多元角色的旗美社大,也總有過多的期待。
而張正揚則認為,有人將旗美社大比喻為「旗美的文化中心」,以不精準語言表達出的概念,卻很深得人心。最後,他堅定地表示:「旗美社大以農村是一座學校的主軸不會改變,未來還要以社大的體制持續促成有機的栽種,也串起產銷間的緊密互動。」
在旗美地區,我們看見許多為了相同理念遠道而來的農夫,雖然過程中有的進來、有的離去……,但還是能強烈感受到這條提供立體學習的管道,只會日益增強而不會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