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生要怎麼過活、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Syman Rapongan)始終很清楚。
「現在的我,就是不想待在台灣,」邊抽菸邊啜飲濃咖啡的夏曼,娓娓道出剛過五十歲的自己,只想照著直覺、感覺走,完全不做生涯規劃。
其實,夏曼從小是抱著要到台灣唸大學的夢想,高中畢業後,原本有機會保送上大學,他卻選擇拒絕,來台北南陽街補習兩年半,邊準備大學聯考邊打工,才考上淡大法文系。
「在逐夢的年紀,能實現上大學的夢想,我比較幸運,但還是遇到很多挫折,」夏曼淡淡地說,挫折包括生活上不適應、沒錢讀書而必須打工和搬水泥,現在想起在台灣的那段日子,覺得還真累!
大學畢業後,他以打零工、開計程車維生,但總覺得找不到自己。1988年投入蘭嶼反核自救運動,最後經過一番嚴肅的自省,決定在1989年從台灣回到蘭嶼。三十二歲的夏曼開始重新學習達悟人傳統生活方式與技能,包括潛水、射魚、上山砍柴造舟與蓋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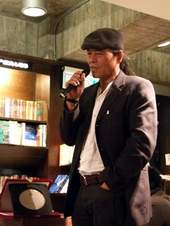
達悟男人潛水射魚造船
回到蘭嶼後,夏曼剛開始曾被族人貼上「退化的達悟族男人」之污名。每天聽到父親說他已退化、被漢化,甚至變成台灣人的評語;母親則要他別天天射魚,總嘮叨說去台灣找個工作賺錢吧。妻子責難他不善於賺錢養家,孩子們抱怨從他身上搜括不到十塊零錢。
夏曼回憶說,父親生前曾強調:「我要詛咒那個男人不去造船,不去抓飛魚,不去抓鬼頭刀魚。」那個男人,也就是夏曼,卻深深被這句話迷住,開始學潛水、射魚,接受海洋的洗禮,也盡情享受對海的愛戀。
在蘭嶼,潛水、射魚、上山砍柴造舟、蓋房子,是所有傳統達悟男人應具備的生存能力。因此當夏曼的潛水、射魚經驗愈來愈豐富,技能也愈來愈厲害,便逐漸被族人接納。
現在他每天都在造船,保存族人傳統工藝,或是下海潛水、抓魚,「我很喜歡下雨天,在這種天氣,沒有人會出海,只有我一個人出海,感覺最棒,尤其是愈寒冷,我愈喜歡孤獨地享受潛水、射魚的甘苦,」夏曼笑說。
更重要的是,當你愈是潛水、射魚的高手時,你的漁獲就會愈少,因為你會選擇你要的魚,而不是濫射。
其實,達悟是很幸福的民族,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海。「生活在蘭嶼是很幸福的,有寬闊的海洋,即使很鬱卒、心情不好,可以去看海、潛水,轉換情緒,我是一個很放任自己的人,生活在蘭嶼才適合我的性格。」夏曼解釋說。
航海流浪拍紀錄片
夏曼的父親曾問他:「你何時愛上我們的海?從你出生捧在手掌上那一刻,我就按祖先的習俗說:『讓我的長子像海那樣的堅強,像海平靜時那樣的令人心怡。』按祖先的習慣,達悟的男人絕對要愛海,和海洋做朋友……。」「孩子,你要養成愛慕海洋的性格,因為海洋的關係,才有我們這個民族。」
身為海洋民族的達悟人,終究是離不開海的。也因此,夏曼兒時就夢想去流浪,2005年他參與了「飛拉達悟」號從印尼啟航展開的環太平洋之旅,終於實踐冒險的夢想。
不過,航海的夢想能成真,得要感謝他的太太希南.藍波安,因為也是達悟族,更能感受、放任他完成想做的事。說到那個女人,夏曼不禁笑了起來,臉上的線條也柔和許多,「日本朋友曾對我說,你一定要愛你的太太,我說我們達悟族是有恩情的,講恩情,不講愛情。」
目前夏曼手上在籌拍三部紀錄片,與英國BBC、台灣公視合作,內容關於和海的關係、造舟、人文和自然(民族植物)。今年五月則要拍攝航海紀錄片,與導演林正盛合作,將2005年前往印尼、菲律賓等南島語系國家的航海故事記錄下來。
 每句話都有海洋影子
每句話都有海洋影子
「然而,當我穿上潛水衣,決定潛水射魚時,惡靈是阻止不了我的。海,畢竟是我這一生的最愛。三年來,我已經習慣一個人潛水射魚,除了興趣外,我真的很難形容自己游在海裡那種興奮的心情。」
「海,是有生命的,有感情,溫柔的最佳伴侶。海中形形色色的奇景,唯有愛她的人才能感受她赤裸的艷麗與性感。」
「海,是一首唱不完的詩歌,波波的浪濤是不斷編織悲劇的兇手,但亦為養育我們的慈父。我們深愛著海洋,同時也深怕著海流。我賴以維生的大海,我願做勇敢的孩子,依偎在的胸膛。」
「不潛水,就無法體驗到族人與魚之間親密關係孕育出的海洋文化。」
夏曼出生於蔚藍海洋環抱的「人之島」,從小每天與海為伍的背景,反映在他細膩優美、充滿詩意的筆下,於是海洋、飛魚、傳統達悟人的生活智慧和悲喜,成了他作品的核心。身為台灣原住民中唯一的海洋民族,達悟男人們的思維中,以及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海洋」的影子,也因此海洋的變幻莫測,自然而然成為夏曼取之不竭的創作泉源。
在文學評論家眼中,夏曼的創作,在「有海洋氣味的作品」上獨樹一格,深具特異的魅力。無論是寫海洋的神秘多變、寫捕捉飛魚的生命躍動、寫歷盡滄桑的達悟民族,都讓人輕易的且在不知不覺中,從字裡行間掉入達悟人的海洋觀裡。
《冷海情深》、《海浪的記憶》是夏曼描寫身為達悟族的他,重返蘭嶼學習潛水捕魚、伐木造舟,學做一個真正的達悟男人、達悟勇士的故事。
從這兩本書中,可以強烈感受到夏曼對於亟欲追求達悟傳統生活方式、建構達悟族海洋哲學的焦慮。在一開始,他急於彌補離開故鄉之後的文化斷層,卻得不到父母與妻小諒解的寂寞與苦悶。直到潛水捕魚的技術更精進、對海洋多一分了解,才讓他贏得族人及父親長輩們的認同,也愈能感受到身為達悟人的驕傲,體驗海是所有深情與驕傲的源頭。
當作家要學習反省
 從2002年出版《海浪的記憶》後,夏曼好久沒出書了。現在的他,還是斷斷續續寫文章,隨筆寫下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比如蘭嶼古老的職業、造船、種地瓜和芋頭。
從2002年出版《海浪的記憶》後,夏曼好久沒出書了。現在的他,還是斷斷續續寫文章,隨筆寫下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比如蘭嶼古老的職業、造船、種地瓜和芋頭。
夏曼說,身為海洋文學作家,總是會思考一個作家究竟要帶給讀者、民族、社會什麼樣的影響,同時也要激勵自己擴大讀者群,「讓讀者不再把海洋想像得很恐怖,也進入達悟人的海洋觀裡,就算很成功,起碼我做到這一點。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對自己成長的環境、土地、民族的熱情,絕對不比任何人少。」
「我的學生曾跟我說,『老師,看到你,就會想要吃魚,想到蘭嶼灰色的天空和藍藍的海洋』,」夏曼笑說。在創作上,儘管不是多產的作家,但仍給自己期許和壓力,希望不論是小說、隨筆或小品,都要讓人有所共鳴,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看到他的文章,就會產生共鳴。
談到作家的責任,夏曼很肯定的說:「一個作家是需要反省的,我給自己空間、時間反思,而且在蘭嶼也是需要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