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台灣東南方海上的美麗小島─蘭嶼,20年前曾在達悟族的力抗下,進行反核運動;而10年前由關曉榮以向弱勢者認同、試圖貼近的凝視與反省,拍攝而成的紀錄片《國境邊陲》,不只是人民運動不可或缺的力量,還是達悟族人用自己的血淚書寫出的生命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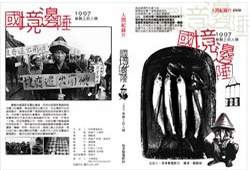 老題材卻有許多素樸心意
老題材卻有許多素樸心意
《國境邊陲》的影像紀錄,讓達悟族人的生活與勞動、讓人與自然的關係、讓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人唱什麼歌,以最純真質樸的形式如實地表現出來。而導演關曉榮在片中關注的則是「達悟族人製作傳統拼板舟的過程」與「當年反核廢的人民運動」。而選擇在拍攝10年後才對外發行,關曉榮說:「除了當時資源不足難以展開宣傳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從過去事件來觀察社會的變遷,以及反思資本主義對邊陲的推擠。」
而關曉榮開始投入台灣少數民族的拍攝,則緣起於他在跟原住民相處時感受到的「原住民被殖民、被列強侵略的經驗。」有一回,他因採訪之故而到屏東霧台鄉,在路上碰到一群年輕人還熱情邀約他至家中住宿,當天他們則一起在月光下聊天、喝酒度過一個相當愉快的夜晚。隔天,當又碰見前晚熱情與他攀肩搭背的年輕人時,竟轉而為防衛性的冷漠態度,讓他為此困擾許久。於是,他自揣:「酒精讓原住民青年暫時卸下民族心靈創傷的芥蒂,但是,漢人與原住民間的緊張感卻是始終存在的。」也因此引發紀實攝影者關曉榮內在的精神風暴。
1987年,漢族的關曉榮辭去周刊記者的工作,開始進行蘭嶼的系列報導攝影工作,並分篇寫成〈一個蘭嶼能掩埋多少國家機密〉、〈雅美十人舟的榮耀〉、〈塵埃下的薪傳燼餘〉、〈文明在仄窄的樊籠中凋萎〉、「飛魚祭的悲壯哀悲〉、〈漢化主義下的蘭嶼教育〉、「流落異鄉的雅美勞工〉、〈酷烈的壓榨悲慘的世界〉、〈被現代醫療福祉遺棄的蘭嶼〉、〈觀光暴行下的蘭嶼〉與〈孤獨傲岸的礁岩〉共11篇的紀實攝影,陸續發表於當時台灣第一本以報導攝影為主的《人間》雜誌。
1997年由「侯孝賢電影社」出資,關曉榮執導的紀錄片《國境邊陲》才開始拍攝,隔年便剪接完成。當年侯孝賢支持拍攝的想法是:「文字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如能以原始、自然的影像捕獵方法完成,每一個人的知識拼圖就又會更齊全一些。」
而後,因尋求宣傳與聯映事務皆不順遂,加上關曉榮開始到「台南藝術大學」擔任教職,致使影片相關的後續製作及行政工作難以順利推展。直至2006年夏天,「夏潮聯合會」在蘭嶼舉辦的文藝營,讓《國境邊陲》又有了面世的機會,過程中因佳評不斷,而激發了由「人間學社」發行的想法。
解放歷史 創造能量
 自1987年2月20日,蘭嶼達悟族開始驅逐「蘭嶼惡靈」的反核廢料抗議示威活動,至今已歷經20年,這20年來位於國境邊陲的蘭嶼達悟族仍然在核能廢料這個惡靈的恐懼下生活。除此之外,當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改變了達悟族固有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時,他們的環境與民族文化散失的問題更是值得關注。
自1987年2月20日,蘭嶼達悟族開始驅逐「蘭嶼惡靈」的反核廢料抗議示威活動,至今已歷經20年,這20年來位於國境邊陲的蘭嶼達悟族仍然在核能廢料這個惡靈的恐懼下生活。除此之外,當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改變了達悟族固有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時,他們的環境與民族文化散失的問題更是值得關注。
以當年統治權力錯誤的民族政策,理所當然地將核輻射廢棄物棄置在這國家意識與統治權力薄弱的國境邊陲,揭開資本主義商品體制下強勢對弱勢殘害的問題。例如:達悟人世居的蘭嶼家鄉差點成為核廢料儲存場,整個族人居於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弱勢,與年輕族人為了謀生而被迫離鄉、流離於異鄉台灣,又或者是飛魚文化的散佚……等。
人、海、魚、歌、勞動、生活、島嶼,構成關曉榮作品《國境邊陲》的音畫要素,在多重辯證、交織出蘭嶼反核廢運動發動10周年後達悟族人的處境。如今紀錄片《國境邊陲》重新出土,除了再現過去思想、情感和實踐的記憶,也需要觀看者以貼近文本的閱讀方式,謙卑的觀看、同理的對話,並將自己變成關懷與學習改造的一部分,從緊張中帶出感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