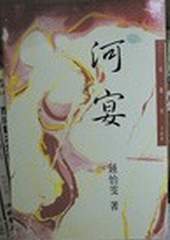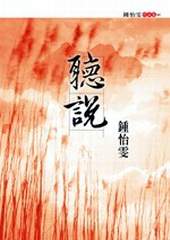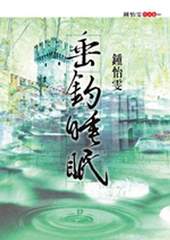曾經以《垂釣睡眠》、《給時間的戰帖》榮獲時報與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的鍾怡雯,文壇曾有人盛讚其為「文界哪吒」,散文風格擅從細微處觀照大千世界,洞悉力過人。去年七月出版的《野半島》,極具個人傳記寫實的風格,樸實地呈現出這位馬來西亞華僑作家的特殊成長背景,如何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生活環境中,涵養出豐富奇幻的家族歷史,讓鍾怡雯在書寫過程中,看見了家族的生命力。
曾經以《垂釣睡眠》、《給時間的戰帖》榮獲時報與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的鍾怡雯,文壇曾有人盛讚其為「文界哪吒」,散文風格擅從細微處觀照大千世界,洞悉力過人。去年七月出版的《野半島》,極具個人傳記寫實的風格,樸實地呈現出這位馬來西亞華僑作家的特殊成長背景,如何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生活環境中,涵養出豐富奇幻的家族歷史,讓鍾怡雯在書寫過程中,看見了家族的生命力。
頓悟遠離家鄉的感受
由聯合報副刊、聯合文學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主辦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心事──又見女作家的生活與寫作」系列講座中,鍾怡雯是唯一來自海外的女作家。外界曾經認為《野半島》是個人的回憶錄,但鍾怡雯表示這還不是個人回憶錄,她認為此刻尚非撰寫回憶錄的絕佳時刻;只是,《野半島》去年七月出版的時間點,對她來說,獨具意義。
19歲那一年,她拋棄一切,遠離居住了19年的馬來西亞,隻身來台讀書,而去年也正好是她來台求學工作屆滿19年的時刻,這兩個剛好對等的「19年」,意義特別,終於頓悟曾經想盡辦法遠離的家鄉,對她產生了意義,也讓她看見自己在台灣同輩作家中的位置在哪裡。
鍾怡雯表示,寫散文是非常透明的,它牽連著家族、命運和血緣,以及看不見的祝福或咒命,如此貼近到一個人的生命故事,而童年對作家來說是很重要的。鍾怡雯是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客家後裔,她的思考模式和生活習慣不同於台灣作家,曾有人形容她過著隱居生活,對於如此說法,鍾怡雯不甚認同,自己只是比較少與藝文圈人士來往。
鍾怡雯認為她期待過一個奇特的生活,目前渴望在生活中去做到以前不曾做到的事情,曾經她反省是否性格太孤僻,後來體悟到這是因為生命前19年的重量太大了,它形塑出一個人的個性,近幾年鍾怡雯開始慢慢去回觀童年經驗,她知道那是以前生活痕跡產生的行為。
嚮往外在世界的逃家者
從馬來半島搬遷到台灣這座島,從連繫著家族的地方移動到完全陌生之地,年輕的鍾怡雯只有一個明確目標:就是離家,不管到哪裡。身為家中老大,背負著長女的原罪,鍾怡雯受不了家的管束,受不了油棕園把她當成犯人一樣囚禁在無邊無際的綠海,受不了溺斃和窒息之感,遂成為逃家的人,當初的反抗其實很單純,嚮往外面的世界,不想被綁在家裡頭。她在《北緯5度》序文中這麼解釋離家的原因。
「父親不理解他這輩子的痛苦來自祖父有效的教導,聽從,順服,鍾家斯巴達式的家規。祖父的痛苦來自曾祖母的遺傳,如果我當乖女兒,那麼,我的下場就跟父親一樣:他嚮往自由,卻聽從順服祖父,遺傳曾祖母的瘋狂和極端,這些條件的組合成為父親的宿命。唯一一次的叛逆,是離開錫礦湖離開老家南下自立門戶。祖父罵了幾個月,說他沒出息,比不上坐寫字樓的大姑丈,也不如當警察的二姑丈。做粗工哪裡做不都一樣?跑大老遠幹嘛?」鍾怡雯說。
當年偷偷摸摸出國,沒有告知祖父,導致家族風波難息。曾經扛著笨重的大行李,母親和妹妹陪她搭公車去火車站,而這段離家的記憶,多年後竟然憑空消失,她完全忘記了那個當下的行為,自己是連回過頭向家人說再見的意願都沒有,因為那一刻她的心不再眷戀,鍾怡雯曾問自己「我不愛家嗎?」, 她知道自己不是這樣的人,她渴望的是自由,她被關在油棕園太久了,家庭氣氛框住了她,看不到盡頭,所以一心一意想要離家。
從馬來半島到台灣島
 從小鍾怡雯的生活周遭有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從多元文化的複雜環境來到單一文化的國度,從熟悉的環境來到陌生之地,來到兩個都是「島」的國度,之間的差異給了鍾怡雯回去觀照家鄉的空間,她是到了他鄉才漸漸地知道故鄉對於她的意義,這也是她之所以書寫《野半島》的原因。
從小鍾怡雯的生活周遭有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從多元文化的複雜環境來到單一文化的國度,從熟悉的環境來到陌生之地,來到兩個都是「島」的國度,之間的差異給了鍾怡雯回去觀照家鄉的空間,她是到了他鄉才漸漸地知道故鄉對於她的意義,這也是她之所以書寫《野半島》的原因。
在書寫過程中,鍾怡雯最大的發現是,她看見了生命力。鍾怡雯說「時間和空間拉開距離。因為離開,才得以看清自身的位置,在另一個島,凝視我的半島,凝視家人在我生命的位置。疏離對創作者是好的,疏離是創作的必要條件,從前在馬來西亞視為理所當然的,那語言和人種混雜的世界,此刻都打上層疊的暗影,產生象徵的意義。那個世界自有一種未被馴服的野氣。當我在這個島凝望三千里外的半島,從此刻回首過去,那空間和地理在時間的幽暗長廊裡發生了變化。鏡頭一個接一個在我眼前跑過,我捕捉,我書寫,很怕它們跑遠消失。我終於明白,為何沈從文要離開湘西鳳凰,才能寫他的從文自傳。」
家鄉點滴是最大寫作資產
青春少年的叛逆期,曾經是成長中的痛,儘管存留很多的不愉快記憶,而今離家19年後的她已長成少婦,對於過往成長的痛,看見的已是祝福。家族的種種過往、家鄉的點點滴滴全成了寫作題材的資源資產,近期以來鍾怡雯投入研讀有關於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文獻資料,並準備親赴馬泰邊境進行研究。展開這項計畫的主要原因在,鍾怡雯始終懷疑自己的祖父其實是共產黨員,將研究的地區是1989年馬來西亞共產黨投降後被集中到的馬泰兩不管地帶。
鍾怡雯一直在思索祖母為何老是埋怨祖父不顧家,經常行蹤不明,逼得祖母獨力拉拔所有孩子長大,祖父表面看起來是在錫礦場工作,又為何不曾拿錢養家呢?這是非常奇怪的行為,其實原因很可能是祖父的共產黨員身份,祖父很多時間都躲在山裡頭起義抗戰。鍾怡雯研究資料後發現,馬來西亞從對抗英國殖民到抗日,很多戰役幾乎是由客家人率先起義,鍾怡雯記得父親曾說過祖父拿過槍,可惜父親說得語焉不詳,僅含糊說以前住在樹膠林旁邊,每次馬共與英軍或共軍開戰時,住民都必須躲避槍林彈雨,當時死了很多人,等到鍾怡雯回去翻閱文史資料後,才知道原來自己從小居住的村落,很多青年、壯年都是揭竿起義而壯烈犧牲,這讓她興起意念想去找尋祖父的另一個身份。
從書寫《野半島》開始,鍾怡雯驚喜自己的家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野史,奈何長輩們一一離世,很多奇幻情節早已無法追溯,鍾怡雯建議致力於寫作者,務必趁早詢問家中長輩,否則等到終於想寫作的那一天,能夠做的只有拼湊而已。就像祖母曾經懷疑祖父在外頭養女人,前兩年她回去探訪老家樹林房子,那邊有一座廢棄的錫礦場,以前常有貪玩的孩子莫名奇妙溺死在坑洞內,漸漸附近傳出有水鬼的傳聞。連隔鄰老太太的先生有一天不知道為何走進去這座沒有人煙的廢礦廠,也突然暴斃,離奇的是,死亡時的姿勢竟然是呈現站立的姿勢,嚇死附近居民,這讓鍾怡雯決定趕緊去訪問這位老鄰居,而有趣的是,這位老太太正巧是祖父傳聞中的外遇對象。
鍾怡雯表示,《野半島》原打算以長篇小說方式呈現,最終卻成了短篇合集,那是因為她始終寫不出來她想寫的長篇模式,人生有太多記憶是片片段段的,故事是中斷的,她尚無法用完整故事將之訴說出來,所以《野半島》只是過渡的作品,或許下一部作品將可能是以祖父母為主角的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