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屆全國兒童文學、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由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兒童文學專業研究室主辦,承辦單位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台灣文學系邀請學者、專家展開2天的學術研討,針對逐漸落寞的台灣兒童文學及轉型契機提出討論。
 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於6月25、26日,在靜宜大學任垣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會召集人趙天儀教授表示,台灣兒童文學的成長,計有日治時期與國府時期二大階段,從兒童文學各領域來書寫、回顧與展望,期許在兒童文學史的建構,有個嶄新的出發與契機。
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於6月25、26日,在靜宜大學任垣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會召集人趙天儀教授表示,台灣兒童文學的成長,計有日治時期與國府時期二大階段,從兒童文學各領域來書寫、回顧與展望,期許在兒童文學史的建構,有個嶄新的出發與契機。
台灣兒童文學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由陳千武主持,吳麗櫻、林武憲、蔡榮勇、洪中周、廖瑞銘、陳秀鳳、林美琪、邱各容擔任引言人,研討會集結成書出版「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以下是研討會內容重要紀要:
陳千武/兒童文學的重要性
部分文學者的認知,古典文學是沒有所謂的「兒童文學」,現代詩人洛夫說,文學裡沒有兒童文學,詩人余光中也說,散文都寫不好了,如何談到寫詩呢?
他們不知道台灣兒童文學裡面的兒童詩的美,小孩子不知道寫詩;也不知道寫散文,我認為小孩子能夠講話,能夠思考就能寫詩了,詩是我們眼睛看不到的東西,並把它表現出來。
一般人用眼晴來思考,來看東西,來批判、來發表一切,但是,詩卻能表現眼睛看不到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我在擔任文化中心主任時,曾讀到一首童詩,那是國小一年級學生寫的,我至今仍不會忘記,那是描寫媽媽的愛。
愛是看不見的,而詩裡寫著「媽媽的愛是一盆滿滿的洗澡水/我躺在裡面睡著了……」愛就像洗澡水那麼溫暖的東西,愛可以像在洗澡水裡頭,很安心的睡著,詩不是用美麗的語言、文字,而是用自己的心靈發表出來。
台灣文學在日治時期,1923年開始有創作,由於殖民地的形態,創作都是以寫實主義的小說創作為主,詩的表現涉及精神活動,統治者不喜歡讓台灣人用精神活動來描寫、充實生活,這是殖民地的悲哀。
所以台灣早期文學,都是眼晴看到的居多,而眼晴看不到的文學較少,談到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本質等,不管是成人文學或是兒童文學,都應該著重在眼睛看不到的思想表現,讓台灣社會有精神的活動,有精神的交流,讓台灣社會在精神上得到滿足。
吳麗櫻/台灣兒童文學的發展
台灣兒童文學發展是6、70年代開始興盛,1971年,板橋國校教師研習會主任陳梅生博士,召集全國兒童文學創作者與教師,作為期1個月的「兒童文學研究班」集訓,兒童文學的觀念與思潮推向全國,這是一個新的轉捩點。整體來說,台灣兒童文學發展包括4個時期:
(一)3、40年代兒童文學破冰期
日治時期雖施行新式小學教育,但是,殖民地歧視台灣兒童,無法與日本學童享受同樣的教育品質。目前找得到的是,由宮尾進編纂的台灣兒童文庫《童謠傑作選集》,全文以日語書寫,蒐集3800多首。
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採集民間故事童謠,以漢文記錄收錄在《台灣民間文學集》。戰後1948年,國語日報創刊,兒童版同日創刊,零星介紹中國兒童詩與童話,內容著重在教育與推行國語,兒童文學呈現荒蕪。
(二)5、60年代的兒童文學醞釀與草創
兒童文學以宜蘭縣發展最早,1956年,藍祥雲在五結國小編輯出版校刊《青苗》,邱阿塗、黃春明、吳柳彬等人在廣興國小推廣兒童文學研究,1964至1970年,號召全國有志兒童文學教師,舉辦兒童文學研習冬令營,教師義務教導;學生免費學習。
屏東地區的發展也頗早,1956年黃基博等教師為兒童出版《幼苗月刊》。1962年,台中市政府出版《兒童天地》,此外,其餘地區罕有兒童文學;遑論兒童文學的發展。
(三)70年代的兒童文學播種與萌芽
1971年板橋國校教師研習集訓班,舉辦8個梯次研習活動,帶動全國各區域的兒童文學發展。1974年,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與《書評書目》雜誌舉辦「兒童文學創作獎」培植許多兒童文學人才,1976年,台中市文化中心主任陳千武多次為教師舉辦兒童文學研習,帶動全國兒童文學風氣。
1977年,林鍾隆主持《月光光》是台灣第1份兒童詩刊,1980年,《布穀鳥》季刊,參與的成員曾達到267位,是台灣兒童文學史上,最大陣容的兒童雜誌。
(四)80年代兒童文學茁壯與蛻變
經過長期的努力,各地相繼成立兒童文學社團,包括省教育廳與縣市政府設置兒童文學創作獎,廣辦兒童文學刊物及出版兒童文學專輯,各大學院校相繼成立兒童文學專業研究室等。
兒童文學發展至今,中國與翻譯作品大量湧入,本地作家及作品遭到排擠,而過去教育體系大量植入中國意識,讓兒童文學缺乏土地風情的描述,要表現台灣主體性的兒童文學作品,是大家要努力的目標。
林武憲/台灣兒歌的創作與研究淺說
《兒童詩歌》包含童詩與兒歌,我認為,童詩與兒歌在兒童文學,是不同的兩種文類,雖然很多學者不盡認同。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古代詩歌同源,詩歌不分,後來,詩詞曲的多樣化,詩與歌已不能不分家了,詩是詩;歌是歌,這也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了。
兒歌,有傳統兒歌、現代創作兒歌。兒歌是啟萌教材,是學前教育的好工具,兒歌為兒童打開學習大門,引導兒童進入文學樂園和知識殿堂。在台灣兒歌並不受到重視,因此創作、研究、推廣都遠不如兒童詩,台灣兒歌與歐美及日本相較,實在差得太遠了。
行政院文建會開辦兒歌100徵選後,台灣兒歌多樣化,包括國語、台語、客語、原住民兒歌創作,讓我們自己可以唱自己的歌,不必唱外來的翻譯。台灣兒歌的創作,早期,有蕭良政詞、吳開芽曲的「造飛機」、陳石松的「三輪車」、周伯陽的「妹妹背著洋娃娃」。
台語兒歌有汪乃文的「搖嬰仔歌」、「落大雨」等,早期的兒歌台語與國語皆有,直到推行國語運動,大家就不敢寫台語兒歌了。
蔡榮勇/台灣兒童詩與少年詩
小孩與兒童寫的詩是兒童詩,大人寫給小孩子看的是少年詩。
台灣兒童詩與少年詩發展至今,現在就像是個尾聲,發表的空間與出版品太少了,指導者也出現斷層現像,讓兒童詩的生存空間縮小。現在只有台中市、彰化縣與農委會等舉辦零星兒童詩比賽。
國語日報周日兒童版與台中市《兒童天地》,有提供少數的兒童詩版面。詩對兒童文學的影響很大,沒有發表園地,寫的意願少了,沒有指導老師,要兒童寫詩幾乎不可能,現在的兒童詩與少年詩,質與量都無法與過去相比。
實施九年一貫教育之後,學生忙著學英文,電腦普及之後,學生不願寫,只要在電腦前,按幾個鍵,就有很多的文章,現在的學生只要看;不願意寫作,或是看得懂;不會寫,我很擔心,台灣會像日本一樣,新生代出現「新文盲」現像。要說這些話,我的內心有些悲傷。
現在的兒童繪本太多了,兒童寫作的空間縮小,出版社不該只是大量翻譯繪本,也要翻譯國外的兒童詩,歐美、日本,甚至東歐與蘇聯都有很好的作品,同樣的,台灣的環境,指導者也出現斷層,歐、美的兒童詩已延伸到幼稚園,台灣的發展有停滯現像,希望可以再看到文學扎根的工作。
廖瑞銘/台灣兒童劇
兒童劇場是西方20世紀的產物,台灣逐漸蓬勃發展,但也還在摸索階段。兒童劇是以兒童的身體、心理為主軸發展的劇場。台灣的劇場史,分為戰後的反共抗俄政治劇、1960年代的教化劇場、1980年代之後的現代劇場。
1980年代之後,戲劇系畢業生開始投入,超出政治、教化的束敷,兒童劇場受到幼教單位與基金會的支持,讓台灣兒童劇場蓬勃發展。1983年陳玲玲的「方圓劇場」製作「老柴、老婆與老虎」等三部兒童劇,開啟大人演戲給小孩看的風氣。
台灣兒童劇的創作形式,受到戰後的政治戒嚴,及國語政策影響,使得文學、藝術的題材政治化,兒童劇也不能倖免,演出的劇本全是國語,主旨設在忠孝節義,內容是清一色的「寓教於樂」。
隨著創作題材多元化,中西劇場的交流,兒童劇場朝著生活化、國際化、社區化發展,演出者也以當地母語演出,不僅演出者對當地歷史有深刻的體驗,同時也凝聚當地社區意識。
陳秀鳳/台灣圖畫書,你欲行去叨位?
現在是圖畫書蓬勃發展的時代,主要受到政策性的鼓勵與民間出版業者的競爭,初期,台灣圖畫書是受美、日影響,近年來,台灣圖畫書走入國際舞台越來越明顯。
義大利波隆納國際兒童書展年度畫家,台灣已超過20人次獲選,格林出版社引進國際知名插畫家,開拓台灣插畫者的繪圖能力,陳致元的《小魚散步》、《GUJIGUJI》成功打入美國市場;李瑾倫首例成為英國WALKER出版社簽約的插畫家。
台灣圖畫書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但是台灣圖畫書在教育上,卻又出現要求學生寫感想等延伸活動,讓原本歡喜相遇的圖畫書,又走向灌輸教育意涵、道德觀的老路,側重圖畫書「文字」的解說與詮釋,反而忽略「圖畫」的藝術薰陶及表現。
品嘗閱讀是美好的,使其成為完全的人,生命教育就該像幸福的種子,讓兒童自由自在的閱讀,未嘗不是更重要的生命教育。另外,圖畫書是否要附送導讀的論戰,透露大家對圖畫書有不同的詮釋,我們應該把圖畫書歡喜相遇的權利,還給台灣的兒童,透過常態閱讀的圖畫書,進行生命教育,才不至於失去原本的靈魂。
林美琪/台灣的世界兒童文學翻譯
從3本書來看世界兒童文學翻譯,《黑鳥湖》(The Witch of Blackbird Pond),那是描述清教徒及移民者的國家認同問題,黑鳥湖所提供的態度,正是美國新移民的心態,人應該忠誠於在他腳下及眼前的土地,《黑鳥湖》提供台灣新海洋國家及兒童讀者重要的信念。
《鬧鬼的夏天》(Ghost of summer),故事以北愛爾蘭新天主教徒的衝突為背景,用懸疑的手法描述北愛爾蘭的宗教、政治問題,台灣的兒童文學罕涉及國際政治主題,透過翻譯帶給兒童讀者新的國際觀。
德文作品《會飛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傳達智慧、勇氣和友誼的價值觀,這是一本探討《自我認同》的書藉。我認為,兒童所處的世界與成人世界是相同的,不要輕忽小孩的認知能力,台灣的政治議題在兒童文學創作一直是個禁忌問題,應多元、適度開放給兒童認知。
邱各容/我如何撰寫台灣兒童文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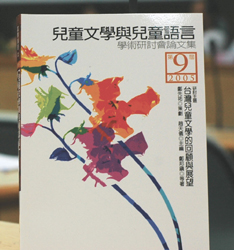 我撰寫《台灣兒童文學史》,希望能對兒童文學有所助益,也做為日後學術研究的參考。台灣兒童文學史是首部以兒童文學為史料研究,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兒童文學與日、韓、菲、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地區來往與交流。
我撰寫《台灣兒童文學史》,希望能對兒童文學有所助益,也做為日後學術研究的參考。台灣兒童文學史是首部以兒童文學為史料研究,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兒童文學與日、韓、菲、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地區來往與交流。
這些國家都有兒童文學史的出版,唯獨台灣沒有,主要原因是,台灣投入兒童文學史的研究太少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即將出版《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有關台灣文學史排入第19章,篇幅約有80頁,遠超過中國以往出版的各書。
如果,我們不先出版自己的兒童文學史,那就失去歷史的解釋權,自己人寫自己的兒童文學史是名正言順,也是對自我的一種責任。《台灣兒童文學史》的問世,最大的意義是搶救兒童文學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