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30日的一場車禍,奪走了洪醒夫的生命,以他在世33年的歲月所留下的文學作品,已然是台灣現代文學的瑰寶。洪醒夫如果不死,今年58歲了,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他的人生歷練一定會更深刻,書寫出更經典的台灣文學作品。
抑或是老天爺不願讓他看到這25年來的台灣,只好讓我們對台灣鄉土人物的記憶,隨著他的作品逗留在20世紀的60、70年代,這無非令人感傷的。
15歲立志當作家
洪醒夫,本名洪媽從,1949年出生於彰化二林,算是戰後的一代。這一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50年代,台灣文壇瀰漫在一片反共文學的氛圍中;60年代則興起了現代主義文學的風潮。70年代,社會意識的覺醒,引領反映台灣社會現實的鄉土文學抬頭,卻也引來「工農兵文學」的撻伐。洪醒夫的童年在50年代度過,文學的成長與成名則在60、70年代。13歲離開純樸的二林鄉下負笈台中,15歲立志當作家,18歲寫第一篇小說〈逆旅〉發表於《台灣日報》,到他33歲逝世,15年間,可以肯定的說,他並未直接經過現代主義的洗禮,也未曾參與鄉土文學的論戰,然而作品中所呈現的,不無受到這兩股文學潮流的影響。
但是對他產生衝擊的,還是他從二林鄉下到台中都市求學的階段。1977年,洪醒夫在《聯合報》發表的〈瑞新伯〉中寫道:「有一個秋天的黃昏,我低頭走過台中火車站的天橋,突然有個十分熟悉的聲音拉住我的腳步,循聲望去,叫我驚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看到瑞新伯了,他蓬頭垢面坐在天橋上,衣衫髒破得無法形容……面前擺一個舊飯盒,裡頭零零散散有些鎳幣。」「以後我還在村子裡見過他幾次,都穿得很講究,仍然告訴別人他在當總經理,仍然談笑風生。我始終沒有把天橋上的事情告訴別人。」貧窮的農村,繁華的都市,「我想,它一定擊痛了我的什麼地方。」〈瑞新伯〉也衝擊著這個世代從鄉下到都市的每一個年輕人。社會的變遷,價值觀的改變,洪醒夫用他樸質而粗糙的文字和無法適應的心理描述這一切,「大家都在欺騙自己,他也是,每個人心裡都很清楚,就是無法承認,無法面對。」〈散戲〉。
因此,洪醒夫生前文友陳義芝在〈與洪醒夫有關的記憶〉裡寫道:「洪醒夫的重要作品,無一不處理窮困這一主題,人被逼入絕境,在窒息的氛圍裡顯露骨氣的宿命觀。那麼深厚的人道主義小說,當年不多人寫,現在更沒人寫得出了。」
另外,陳義芝也寫道:「他算是成名早的作家,參加文學獎,並非想建立什麼灘頭堡,多半只為賺一筆獎金。」即使是這樣,「但醒夫是自我約束力頗強的一個人,他絕不肯把自己不滿意的作品拿出來印成一本書,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一方面認為他是多產作家,一方面遍尋他的小說集子,找來找去卻僅得兩本──《黑面慶仔》和《市井傳奇》。」(隱地〈洪醒夫的三本書〉)稿費對洪醒夫而言是非常美麗的收入,但是不甚滿意的小說則用筆名「馬從」發表。
獲兩大報文學獎 嶄露頭角
1969年他和蘇紹連、蕭文煌創辦「後浪詩社」,用「洛堤」或「司徒門」之筆名發表詩作;1974年,因好友陳恆嘉擔任《書評書目》月刊主編,洪醒夫受聘為特約記者;1975年,編《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扛〉獲吳濁流文學獎佳作獎,此後洪醒夫的創作集中於小說;1977年,助理《台灣文藝》編務,〈黑面慶仔〉獲聯合報小說獎佳作;1978年,〈吾土〉獲第一屆中國時報文學獎優等獎,〈散戲〉獲第三屆聯合報小說獎第二名。
成名給洪醒夫帶來更大的創作壓力,卻也讓他更虛心的向前輩作家請益以求指點迷津,他生前好友王世勛在《懷念那聲鑼》的前言中寫道:「他經常出入東海花園,與楊逵老先生談論文學在這個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學是否有、或者應該有其功能。」鍾肇政、鄭清文、李喬、姜貴都是洪醒夫請益的前輩作家,洪醒夫傳承並延續了台灣前輩本土作家的文學精神。
洪醒夫在他的文學創作生涯中,選擇了他生長,卻受到時代潮流衝擊的農村為主要描述。尋找田莊人的尊嚴,卻也凸顯台灣農村在變遷中的苦難,洪醒夫在《黑面慶仔》的自序中如此寫道:「我自小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印象深刻,寫作時,他們的影像清晰的浮現出來,所以特別感到溫馨與親切。」痛苦而又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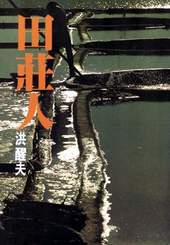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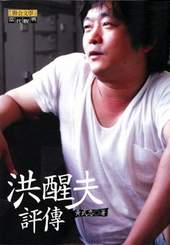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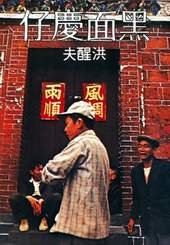
太早出現的人生句點
在他生前,朋友戲稱他為「司徒門洪醒夫斯基」,即是認定他有朝一日定能媲美「杜斯妥也夫斯基」,可惜不假天年,讓他在33歲那年因車禍而喪生。
洪醒夫生前結集成書的只有《黑面慶仔》(爾雅版)、《市井傳奇》(遠景版)兩本小說集,逝世後,第三本書《田莊人》才由爾雅出版,並收錄了未完稿〈焚髮記〉;第二年1983年,好友王世勛編輯的《懷念那聲鑼》由號角出版社出版;1992年,前衛出版社出版《台灣作家全集》收入《洪醒夫集》;2001年,彰化縣文化局出版由黃武忠、阮美麗主編的《洪醒夫全集》九冊,勉強蒐集他大部分的作品,卻是他定稿。
25年前的一場颱風、一場車禍,讓33歲的洪醒夫英年早逝,使得台灣一顆剛升起的文壇巨星遽然隕落!醒夫啊!醒夫!怎忍長睡?令人長歎!
最可貴的是,洪醒夫逝世後,他生前非常知遇的隱地先生─也是小說家、爾雅出版社發行人,為他設立了「洪醒夫小說獎」,雖然後來不克延續,卻也為台灣文壇立下一個典範。
(後記:我因在圖書出版業工作,而於洪醒夫逝世前一年和他認識,包括車禍時和他同車的利錦祥兄都是共同的朋友。那一年的7月29日,我到南部出差,本擬北上時轉至豐原三民書局,卻因颱風而直接回台北,沒想到第三天聽到消息,和朋友趕到豐原的醫院,聽錦祥兄言已回天乏術,做為洪醒夫生前晚期認識的朋友,對他的認識其實是有限的,然值此25週年祭,謹就手邊有限資料寫點紀念他的文章,兼作懷念。)